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多散见于司法解释之中。我们结合法律规范及司法实务,选取了金融犯罪领域的五类典型的非法经营行为展开研究,分别是: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经营期货业务、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使用POS机等方法实施信用卡套现业务以及非法经营外汇业务。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都可构成本罪。另外,该罪属于结果犯,构成该罪要求达到“情节严重”的立案标准。
为更好掌握司法实务中对非法经营罪定罪量刑等方面的关注重点,我们对重点案例进行详细解析,通过研究司法机关的裁判思路,提炼了司法实务裁判要点。同时,我们梳理了与非法经营罪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立案标准及政策法规等规定。
一、实务解析
(一) 非法经营金融业务的行为模式呈现出多样性特征
非法经营罪素有“口袋罪”之称,有研究统计显示,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行为多达70余种。在非法经营金融业务领域,我们结合法律规范及司法实务,选取以下五类较为典型的非法经营的客观行为进行研究。
1.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在我国,证券承销、证券保荐、证券经纪以及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均属于特许经营业务,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从事上述证券业务则涉嫌非法经营罪。例如,超越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经营范围,未经法定机关批准,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代理销售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情节严重的,涉嫌非法经营罪。
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中,比较常见的是非法经营证券经纪业务、非法经营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证券经纪业务主要是指接受客户委托代理买卖证券,包括:为客户开立账户、证券委托交易、数据查询等业务。证券融资融券业务主要是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客户买入证券或者出借证券供其卖出,并收取担保物保证融资不受损失。
司法实践中,部分非法从事证券业务的行为会同时涉及到证券经纪业务和融资融券业务。以场外配资为例,非法场外配资行为因同时涉及非法经营证券经纪、证券融资融券业务而被认定构成本罪。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场外配资作出如下界定:“场外配资是指以高于投资者支付的保证金数倍的比例向其出借资金,组织投资者在特定证券账户上使用借用资金及保证金进行股票交易,并收取利息、费用或者收益分成的活动。”
场外配资涉嫌本罪主要有三种行为模式:(1)系统分仓模式,即当融资方缴纳保证金后,配资经营者向客户分配分仓系统的虚拟子账户并转入本金和配资。融资方通过子账户发出交易指令,分仓系统再委托证券公司下单。(2)出借账户模式,即当融资方交纳保证金后,配资经营者将客户本金和配资转移至其控制的账户并将账户出借给客户,使客户可以通过真实的证券账户下单交易。(3)客户账户模式,即配资经营者将配资转入客户账户,客户在自己的账户下单交易,配资经营者享有平仓等操作权利。
场外配资的系统分仓模式既涉及证券经纪业务,又涉及融资融券业务,出借账户模式、客户账户模式均涉及融资融券业务。行为人在未取得证监会批准的证券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从事上述证券业务,均有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除此之外,如果行为人未经批准,擅自接受委托,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代理销售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或者股票,也涉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犯罪。
2.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是指有关公司或个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交易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或者擅自从事期货业务,或者组织变相期货交易活动的行为。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情节严重的,涉嫌非法经营罪。
从司法实践来看,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行为方式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非法设立期货交易所,另一类是非法开展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其中,非法设立期货交易场所表现为三种形式:非法设立商品类交易场所、非法设立邮币卡类交易场所、非法设立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
非法设立商品类交易场所,主要包括分散式柜台交易和现货连续(延期)交易。分散式柜台交易,指交易场所按照做市商的模式组织交易活动,一般采用高倍杠杆比例进行交易,交易合约具有标准化特征,交易场所不组织商品流通,也不发现商品价格。现货连续(延期)交易实质也是杠杆交易,允许投资者通过每日支付一定费用无限延后交割期限,并可以通过平仓退场免除交割义务。
非法设立邮币卡类交易场所,是指以邮票、钱币、磁卡等为交易对象,供客户申购,摇号中签确定申购后次日开始连续集中交易,交易环节中,采用T+0交易、连续竞价等方式在平台开展交易。
非法设立金融资产类交易场所,常见情形包括未经批准交易信贷、票据、保险等金融产品,开展类资产证券化业务,如定向融资计划等。
3.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金融特许专营业务。根据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支付结算办法》,银行是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的中介机构,未经央行批准的任何非银行金融机构及单位不得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直至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及《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非金融机构也可以申请取得支付许可资质。
无论是银行等金融机构,还是非金融机构,如果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须经过金融主管部门批准,且在经营许可范围内严格遵循相应规章制度。如果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情节严重的,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我国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纳入非法经营罪打击范围的立法初衷是为了有效打击“地下钱庄”。地下钱庄未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批准,逃避金融管理机构监管,擅自以支付结算主体的名义直接为交易双方办理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致使大量资金脱离于金融机构的有效监管,是典型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行为。
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列举了三种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方式,分别是:(1)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的;(2)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3)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套现服务的。
4.使用POS机等方法实施信用卡套现业务
信用卡套现行为违反了信用卡使用的规范要求,扰乱了国家金融秩序,因此被纳入非法经营犯罪打击的范围。信用卡套现的表现形式有:POS机套现、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套现、购物退货套现等。其中,POS机套现最为常见。POS机套现,指信用卡持卡人与特约商户相互勾结、恶意串通,联合违反与银行的协议约定,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虚假方式,通过POS机刷卡的形式套取信用卡额度内现金的行为。POS机套现的具体操作又表现为一般套现、以卡养卡、翻倍套现等模式。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行为人违反国家规定,使用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5.非法经营外汇业务
我国《刑法》规范以非法经营罪论处的外汇业务的行为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二是单位采用非法手段为他人骗购外汇;三是居间介绍骗购外汇。
实践中,行为人因非法买卖外汇而涉嫌本罪的案例较为常见。根据相关规定,买卖外汇只能在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进行,没有资质不能经营外汇买卖。如果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购买外汇,即使外汇是他人骗购得来,行为人对此并不知情,只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立案标准,就涉嫌非法经营罪。另外,变相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也难逃《刑法》制裁。例如,行为人安排境外收付美元,境内再收付相应数额的人民币,实则是以外汇和人民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情节严重的,涉嫌非法经营罪。
(二)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自然人和单位都可构成本罪
根据我国《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自然人和单位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需要注意的是,非法经营犯罪的客观行为类型繁多,司法解释针对不同类型的非法经营行为设立的立案标准也不尽相同。在部分非法经营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单位犯罪参照自然人犯罪的立案标准;而在部分非法经营行为的法律规范中,单位犯罪的立案标准有别于自然人犯罪的立案标准。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形具体分析。
(三)本罪属于结果犯,构成本罪须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
非法经营罪属于结果犯,并非所有从事非法经营的违法行为均构成本罪,构成非法经营罪须符合“情节严重”的立案标准。2022年5月15日生效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七十一条明确了各类非法经营行为的追诉标准。以非法经营支付结算业务为例,非法经营数额在5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即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二、裁判要点
要点速览:
01 未经许可代理客户买卖股票,涉嫌非法经营罪
02 未经批准,擅自以出借账户的方式经营“股票配资”业务,涉嫌非法经营罪
03 不具有从事证券业资格,虚假宣传引流并代客交易股票,涉嫌非法经营罪
04 未经批准,擅自向社会公众销售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属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05 不具有经营期货的资质,与客户签订标准化合约,让客户在其设立的平台上进行大宗无实物交易,属于非法经营期货行为
06 不具有经营期货的资质,诱使投资者到交易平台交易,通过高杠杆配置,赚取手续费及“客损”提成,涉嫌非法经营罪
07 超出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居间介绍他人从事境外期货买卖交易,属于非法经营罪
08 非法经营期货后才取得经营许可的,涉案数额应为取得许可前的投资数额
09 非法经营个股期权证券业务,犯罪数额应根据被害人投资的数额计算
10 设立公司以非法经营场外股权期货业务为主要活动,且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淆,应认定为个人犯罪
11 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从事资金支付结算服务,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12 以虚构交易方式向制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为单位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非法资金提供支付结算业务的,涉嫌非法经营罪
13 未取得支付结算许可,搭建“第四方支付”平台,涉嫌非法经营罪
14 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有人直接套现,涉嫌非法经营罪
15 以虚构交易的方式为他人提供“信用卡养卡”服务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
16 在法定的交易场所以外购买外汇,即使外汇是他人骗购的来且行为人并不知情,仍属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17 行为人通过境外收付美元,境内再收付相应数额的人民币的方式实现价值转换,属于变相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18 明知他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业务,仍为其积极提供帮助,涉嫌非法经营罪
19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所得数额难以确定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的千分之一认定违法犯罪数额,并处或单处相应罚金
20 提供真实的交易平台和账户,并通过借款协议出借资金,由客户自主完成期货交易,仅收取配资利息及手续费的,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01
未经许可代理客户买卖股票,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被告单位为客户代理买卖股票的行为,属经营证券业务范围,而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该行为系在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的,故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06年1月至8月,被告单位上海弘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弘某公司)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开展证券资产委托管理业务,在某地租赁办公室作为经营地点,采取在上海市电台某栏目发布广告等方式招揽客户,通过与客户签订《投资管理协议书》并按客户委托管理证券资产总值的2.5%、3%或5%收取保证金等。在获取客户提供的帐户及密码后,由被告人孙某某向员工下达交易指令,在客户证券帐户内买卖股票,被告单位弘某公司按照盈利部分约20%提成。
经查证,被告单位弘某公司接受陈某、周某等38名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总值达人民币1350余万元,非法获利人民币30万余元。
争议焦点:代理客户买卖股票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辩护意见:
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辩护人对指控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均提出本案不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本案被告单位的行为性质不属于证券资产管理,而属于私募资金或委托理财;(2)即使本案属于证券资产管理,其也没有被法律明确规定为属于证券业务范围;(3)即使本案属于经营证券业务,也是行为在先,规定在后。因为法律规定“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不得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是在2006年之后,而本案弘某公司代理客户买卖股票的行为开始于2005年。
法院认为:
被告单位弘某公司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被告人孙某某作为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关于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辩护人所提弘某公司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意见,经核查,本案被告单位弘某公司的业务模式属证券资产管理,被告单位弘某公司及被告人孙某某为客户代理买卖股票的行为,属经营证券业务范围,而被告单位和被告人的该行为系在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开展的,故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且本案通过在电视台作广告等方式招揽客户,为客户代理买卖股票的行为,具有较强的公开性、影响涉及面广,牟利的目的性明显,具有相关的社会危害性,故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辩护人的上述意见,与事实和法律均不符,不予采纳。
【裁判结果】
一、被告单位弘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
二、被告人孙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
案件来源:孙某某非法经营案【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2008)浦刑初字第876号】
02
未经批准,擅自以出借账户的方式经营“股票配资”业务,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在未取得证监会批准的证券业务许可证、融资融券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以出借账户的方式经营“股票配资”业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6年5月至2017年10月,被告人王某某、毛某某在没有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的融资融券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以某公司的名义向被害人推销“股票配资”业务。
多名被害人同意“股票配资”,并以银行转账的方式交付了保证金,被告人按照1:5左右的比例杠杆提供了潘某某等多人在中某证券、财某证券、九某证券的股票交易账户供被害人周某某、李某某、南某某进行炒股,并对配资资金收取月息2%至3.8%的高额利息。
经审计,王某某、毛某某等人非法经营的涉案金额为3339577元,其中王某某涉案金额2022230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王某某、毛某某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结果】
一、被告人王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被告人毛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
……
案件来源:王某某、毛某某非法经营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人民法院(2020)甘0103刑初134号】
03
不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虚假宣传引流并代客交易股票,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在所属公司不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情况下,行为人伙同他人对外进行虚假宣传,吸引客户前来配资炒股,代替客户进行股票证券交易,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4年4月,尹某一成立永某公司,永某公司在未经证监会批准,不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情况下,让业务员通过打电话等方式联系发展客户,并通过QQ、微信等软件向客户发送股票信息,虚假宣传永某公司有专业的股票分析师和操盘团队、有股票交易内幕消息,引诱客户到公司配资炒股。
根据客户投资的本金和需求,公司向客户承诺配资1倍至5倍不等的金额,与客户签订《借款协议》《委托交易协议》,由客服部员工根据尹某一的指示在股票交易软件上为客户开设账户并代替客户进行股票证券交易。股票盈利后由客户和公司按约定比例分配,亏损由客户自行承担。
经审计,截至2019年1月,共计169名客户参与配资炒股,客户投资总金额25522545.13元,配资总金额为63210000元,委托交易总金额88085000元。
被告人罗某在永某公司担任业务员,按公司要求对外进行虚假宣传吸引客户前来配资炒股,共发展客户3名。其中,客户熊某出资20万元,配资15万元,委托交易总金额35万元;客户陈某出资15万元,委托交易总金额15万元;客户张某出资6万元,委托交易总金额6万元。罗某的违法所得为2.4万元左右。
一审法院认为,罗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三万元。后罗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上诉人罗某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伙同他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依法应予惩处。罗某系从犯,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鉴于罗某已退出违法所得2.4万元,并缴纳罚金3万元,认罪悔罪表现好,符合社区矫正条件,依法可以适用缓刑。
【裁判结果】
……
二、撤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2020)渝0103刑初466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即:被告人罗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三、上诉人罗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宣告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三万元。
案件来源:罗某非法经营案【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2020)渝05刑终674号】
04
未经批准,擅自向社会公众销售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属非法经营证券业务
【裁判要点】
行为人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而设立公司,超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公司经营范围,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代理销售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股票),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03年12月,被告人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为从事非上市公司股票代理销售业务,注册设立被告单位利某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利某代公司)。三被告人通过他人设立的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4家非上市公司代理销售股票,并与该投资管理公司协商确定了每股对外销售价格及内部交割价。三被告人对外谎称上述非上市公司的股票短期内即可上市并可获取高额的原始股回报,并指使其公司业务员向不特定社会群众推销上述非上市公司的股票。
2004年3月30日,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以该公司从事此项业务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为由,作出责令改正并罚款人民币1万元的处罚决定。同年4月,该公司经核准增加了“代办产权交易申请手续”的经营范围,继续代理销售上述非上市公司的股票。
至2004年11月底,利某代公司在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操控下,股票销售总金额达人民币657万余元,利某代公司从中获利人民币240余万元。利某代公司自设立后未从事其他业务。
争议焦点:代理转让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是否属于从事证券业务?
一审法院认为:
首先,被告单位利某代公司及被告人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关于证券经营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我国证券市场实行证券业务许可制度。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国务院办公厅、证监会亦多次明文要求严厉打击以证券期货投资为名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对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非法从事或变相非法从事证券期货交易活动的,以涉嫌非法经营罪立案查处。证监会曾发文明确规定,以非上市公司将要上市并可以获得高额的原始股回报等为幌子,或者编造虚假的公司经营业绩和许诺丰厚的投资回报率等手段,诱骗投资者购买非上市公司股票,从而进行收取代理费等费用的违法活动,属于非法代理买卖非上市公司股票。非法发行股票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的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和金融安全。其主要形式,一是编造公司即将在境内外上市或股票发行获得政府批准等虚假信息,诱骗社会公众购买所谓“原始股”;二是非法中介机构以“投资咨询机构”、“产权经纪公司”、“外国资本公司或投资公司驻华代表处”的名义,未经法定机关批准,向社会公众非法买卖或代理买卖未上市公司股票;三是不法分子以证券投资为名,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诈骗群众钱财。
本案中,被告单位利某代公司并未取得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发的证券业务许可证,但擅自公开向社会不特定群众代理销售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且系拆细发行。在经营活动中,该公司谎称涉案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将要上市、投资人可以获得高额原始股回报,诱骗投资者购买涉案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从中收取代理费等费用,其行为属于非法代理买卖非上市公司股票的违法行为。……利某代公司不具有产权交易的从业资格,并非产权交易经纪机构,被告人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等利某代公司人员亦不具有相应的经纪资格。利某代公司超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既未被授权或许可经营证券业务,又不具备产权交易经纪机构资格,而非法从事证券交易活动,其行为属于非法经营。
其次,被告单位利某代公司及被告人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其他限制买卖的物品,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者批准文件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如前所述,本案中被告单位利某代公司及被告人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的行为属于非法经营行为。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共计向216人代理销售了4家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总计销售未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达188.85万股,销售总金额达人民币657万余元,从中非法获利240余万元。从后果看,涉案购股投资人所购买的涉案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最终能否得到涉案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认可都存在很大问题,极有可能就是废纸一张。可以认定,被告单位及三被告人的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危害波及面广,社会危害性大,已经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
我国证券市场实行证券业务许可制度,未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不得经营证券业务。上诉人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设立利某代公司,未经法定机关批准,擅自接受委托向不特定社会群众代理转让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且系拆细转让,属非法经营证券业务,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三上诉人及其辩护人关于代理转让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不属从事证券业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采纳。三上诉人在利某代公司成立后从事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理转让业务,明显超出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在因超范围经营被处罚后,该公司申请增加了“代办产权交易申请手续”的经营范围,但该项业务仅指接受产权所有人委托,以产权所有人的名义向产权交易机构提出产权交易申请,不包括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理转让业务。根据一审庭审中出示并经质证的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施民某、胡某、范某华及证监会宁波监管局郑某斌出具的情况说明,在2004年5月召开的协调会上,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向三上诉人指出:利某代公司在增加“代办产权交易申请手续”的经营范围后,经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代理转让业务仍属超范围经营,要经营该项业务必须经有关证券监管部门批准。但在此后,三上诉人继续经营该项业务。据此可以认定,三上诉人具有非法经营的犯罪故意……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来源:宁波利某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陈某纬、王某泽、郑某中非法经营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09年第1期(总第147期)】
05
不具有经营期货的资质,与客户签订标准化合约,让客户在其设立的平台上进行大宗无实物交易,属于非法经营期货行为
【裁判要点】
行为人明知其实际经营的公司不具有经营期货的资质,仍然设立网上交易平台,与客户签订标准化合约,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让客户在公司网络平台上进行大宗无实物白银交易,属于非法经营期货行为。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3年4月及2014年2月,上诉人张某先后注册成立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及黄山市乾某分公司,分公司负责人为卢某海。公司实际管理者为张某,卢某海为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市场部总监,负责公司客户开发。以上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咨询服务(不含证券、期货咨询)。
张某购进交易软件,搭建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网络交易平台,指使卢某海等人用拨打电话等方式招募客户或居间代理公司。招募成功后,中某兴泰、乾某公司与客户签订标准格式合同,客户在公司网络平台上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向公司打入保证金,开立个人账户进行大宗白银交易。公司与客户之间无实物交易,交易杠杆比达80倍至100倍,客户根据每次交易标的额向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缴纳200元至800元不等的手续费,交易过程中可双向交易和对冲。客户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打款后,该款项即被转入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账户,而后立即转入张某实际控制的个人银行账户。
经中国证监会安徽监管局认定,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相关经营行为涉嫌非法组织期货交易活动。经审计,2013年4月至2014年8月,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入金共6734.884234万元,出金共6515.8308万元;检察院补充侦查期间,变更指控入金数额为6654.884234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卢某海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宣判后,张某、卢某海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张某、卢某海及其辩护人提出张某、卢某海的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以及卢某海的辩护人提出卢某海没有经营期货的主观故意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在案证据显示,上诉人张某明知其实际经营的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不具有经营期货的资质,仍然设立网上交易平台,与客户签订标准化合约,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让客户在公司网络平台上进行大宗无实物白银交易,属于非法经营期货行为;上诉人卢某海作为中某兴泰公司、乾某公司的市场部总监,明知公司不具有经营期货的资质,仍按张某的安排,积极安排员工招募客户及代理公司,组织员工培训,开展业务指导,在公司经营活动中起较大作用,两上诉人实施的非法期货交易行为违反了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一审法院认定两上诉人的行为均构成非法经营罪定性准确。故此节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上诉人张某、卢某海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结果】
……
三、上诉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四、上诉人卢某海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案件来源:张某、卢某海非法经营案【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皖刑终168号】
06
不具有经营期货的资质,诱使投资者到交易平台交易,通过高杠杆配置,赚取手续费及“客损”提成,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行为人设立公司,在未取得经营期货业务资格的情况下,诱使投资者到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实际与投资人形成对赌关系,通过诱使投资者进行频繁交易以及高杠杆配置,赚取投资者手续费以及对赌的“客损”提成,具备期货交易特征,属于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3年1月,被告人朱某光、朱某杰成立国某贵金属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国某公司);2015年12月,朱某杰注册成立国某盛世公司,随后又成立10余家分公司,分别与多家交易中心公司签约成为其会员单位。在未取得期货业务资格的情况下,招揽投资者到签约公司所对应的交易平台进行“原油指数”、贵金属等期货交易,国某盛世及其分公司向各交易平台指定的账户缴纳保证金。此后朱某杰招募了上诉人黄某胜等人为公司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2016年1月,上诉人李某利成立国某盛世公司鼎某分公司,直属于国某盛世管理,主要负责发展投资者进入到新某大庆提供的交易平台进行石油指数交易。公司成立后,让业务员按照其留下的投资者电话联系投资者,诱使投资者到新某大庆交易平台进行“现货石油”交易。
为发展投资者,国某盛世市场部业务员工通过微信与投资者聊天,诱使投资者到交易平台进行期货交易,并将被告人张某晗等人包装成“资深分析师”推荐给投资者,后业务总监、业务经理、业务员之间按公司的提供的术语相互配合,同时利用投资者高度依赖“分析师”的心理,诱使投资者在交易中每天进行频繁交易,由于配置了33倍交易杠杆,导致多数投资者严重亏损。公司非法获利后,业务员按比例获得投资者的投资经费和交易手续费。业务经理、业务总监及公司高管均按一定的比例获得投资者的交易手续费及“客损”提成。
经审计,深圳国某公司在未取得经营期货业务资格的情况下吸引投资者非法进行期货交易,造成100名投资者损失金额达人民币3301万元。
一审法院认为,黄某胜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万元;云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李某利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宣判后,黄某胜、云某、李某利不服,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设立公司,在未取得经营期货业务资格的情况下,诱使投资者到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实际与投资人形成对赌关系,通过诱使投资者进行频繁交易以及高杠杆配置,赚取投资者手续费以及对赌的“客损”提成,是否具备期货交易特征?是否属于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辩护意见:
黄某胜及其辩护人上诉提出:(1)深圳证监局出具的说明不应成为定案依据。涉案各交易所平台上进行的是现货交易而非期货交易,各交易所不构成刑事犯罪的情况下,作为会员单位的国某系公司员工被追究非法经营罪没有法律依据。(2)即便存在期货交易特征,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各平台的会员单位需要具备期货资质。即便可能存在经营问题,也可以通过民事、行政方式解决,不应直接上升为刑事犯罪。
二审法院认为:
犯罪嫌疑人朱某光、朱某杰等人成立国某系公司并在相关交易平台注册会员单位,平台以路透社、ODS(香港公司)等期货数据为依据,经过人民币汇率和其他一些因素进行转换,由平台进行报价形成价格走势。平台交易的目的是通过价格波动赚取差价,并不是购买真正的实物,平台亦无没有实物交割。上诉人黄某胜等人使用国金系列公司诱使投资者到交易平台进行交易,实际与投资人形成对赌关系,通过诱使投资者进行频繁交易以及高杠杆配置,导致多数投资者严重亏损,赚取投资者手续费以及对赌的“客损”提成。深圳证监局认定其存在担任做市商以集中交易方式进行标准化合约交易且不以实物交割为目的的行为,具备期货交易特征。且国金系公司未均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经营期货业务资格。因此,上诉人的行为符合《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特征。故关于无罪的相关上诉意见及辩护意见,与已经查明的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黄某胜、云某、李某利等人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结果】
一、维持深圳市罗湖人民法院(2019)粤0303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的第一项、第四项;
二、撤销深圳市罗湖人民法院(2019)粤0303刑初385号刑事判决书的第二项、第三项;
……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李某利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百万元……
案件来源:黄某胜非法经营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刑终2680号】
07
超出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居间介绍他人从事境外期货买卖交易,属于非法经营期货
【裁判要点】
行为人成立公司,超出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通过发展代理商、吸引客户到公司提供的经分户软件分户的境外期货账户进行境外期货买卖交易并从中获利,属于非法经营期货行为。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被告人王某一、王某二成立吉某公司。王某一担任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王某二担任吉某公司董事长、监事。
2015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王某一、王某二明知吉某公司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不具备从事经营境内外期货交易业务及居间介绍期货交易资质的情况下,开设多个境外期货账户,并将上述账户设为主账户,绑定境外银行账号,指使工作人员以吉某公司名义招揽客户或二级代理商,再由二级代理商招揽客户的模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推销、介绍境外的期货产品,吸引客户进行境外期货买卖交易。
通过分户软件在主账户下进行分户,客户注册获得账号后,通过在账号内出入金或直接通过王某一、王某二等人的银行账号出入金的形式在境内进行境外期货买卖交易,出入金均以人民币结算。后由结算部人员负责将客户投入的人民币以1:7的固定汇率进行兑换,同时以人民币对美元1:1或1:2进行放大杠杆配资。风控部门负责设置强制平仓功能,确保主账户绑定的银行账户内资金不受损失。在投资人期货买卖交易过程中,收取投资人交易手续费从中获利。
经审计,2015年11月至2018年5月期间,吉某公司在东某证券等5家平台合计成交金额折合人民币3万亿余元,共收取手续费287253339.49元,其中支付居间人的返佣总额1.91亿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王某一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六千万元;王某二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三千万元……宣判后,王某一、王某二等人不服,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成立公司,超出工商登记的经营范围,通过发展代理商、吸引客户到公司提供的经分户软件分户的境外期货账户进行境外期货买卖交易并从中获利,是否属于“非法经营期货”行为?
辩护意见:
被告人王某一的辩护人提出:王某一等人成立吉某公司居间介绍他人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行为,并未违反《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不属于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经营期货”行为,没有扰乱期货市场秩序。原判关于王某一等人非法经营期货的认定错误,王某一等人此节行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被告人王某二的辩护人提出:原判认定王某二等人“在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不具备从事经营境内外期货交易业务的情况下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的相关事实认定错误,吉某公司仅是通过分户软件为客户实现境外期货交易提供一种软件技术服务,王某二等人的行为并不属于“经营期货”行为,王某二等人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王某一、王某二的辩护人针对本案定性提出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经查,工商登记显示,吉某公司登记的经营范围不包括“期货交易”相关内容,在经营范围中明确注明“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出具的《关于杭州吉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证券期货业务经营资格有关情况的复函》证实,吉某公司未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不属于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期货交易所或其他期货交易场所,不具备经营期货业务的资质,亦不具备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经营证券业务的资质。
结合吉某公司组织客户开展非法境外期货交易业务的实际经营情况,可以认定被告人王某一、王某二等人以吉某公司为名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管机构批准获得期货经营资格的情况下,通过发展代理商、吸引客户到吉某公司提供的经分户软件分户的境外期货账户进行境外期货买卖交易,外盘期货依据国际期货交易市场的交易数据结算盈亏,并根据客户出金、入金金额收取手续费等形式从中非法获利。王某一、王某二等人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非法从事期货交易活动,非法经营境外期货业务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三项规定的“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情形,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裁判结果】
一、维持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2019)浙0104刑初156号刑事判决主文第十一项,即对作案工具的处置部分,撤销判决的其余部分。
二、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一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万元。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王某二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万元。
……
案件来源:王某一、王某二等非法经营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刑终600号】
08
非法经营期货后才取得经营许可的,涉案数额应为取得许可前的投资数额
【裁判要点】
行为人设立公司后,在未取得期货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开展期货行为,之后取得期货经营资格的,涉案数额应为涉案单位取得期货经营业务许可证之前投资人的投资数额。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5年11月,被告人韩某峰等人注册成立山东期某公司,后于2018年7月成立财某期货济南营业部,财某期货济南营业部于2018年7月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
经营期间,韩某峰等人除为客户在平台开户进行正常自由交易外,还针对部分客户开展配资业务,即按照客户投资金额1倍至10倍在客户子账户内进行配资,并收取高于正规平台的手续费、交易费,同时按月息一分左右收取配资额利息,被告人陈某澜提供部分配资。为进行期货经营,陈某澜购买麒某资管系统和知某平台软件,客户通过上述软件在子账户内进行期货交易。韩某峰等人招募被告人郭某旭担任讲师,负责分析期货行情,向业务员推送期货专业知识和相关信息。
韩某峰等人为发展业务,要求业务员在网上加入投资期货群,招揽客户到公司的微信群,安排人员扮演讲师角色进行期货分析,其他业务员配合喊单、发专业话术、发虚假盈利图、烘托气氛等,引导客户做配资业务,通过赚取配资业务手续费和利息等方式非法牟利。韩某峰等人按公司获利比例分成,其他业务员的收入为工资或手续费提成。
截至2018年7月,韩某峰等人发展客户进行配资期货交易,客户存入资金约610万余元。一审法院认为韩某峰等人非法经营数额为610余万元。随后,韩某峰等人提起上诉。
一审法院认为,韩某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宣判后,韩某峰等人不服,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设立公司在未取得期货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开展期货行为,之后取得期货经营资格的,非法经营数额应如何认定?
辩护意见:
韩某峰上诉提出:原判将投资人的投资款等同于非法经营金额,认定其行为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对其判处罚金一百五十万元,均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量刑过重,罚金过高。
郭某旭上诉提出:原判对涉案金额认定有误,应认定期某公司收取高于期货公司标准的手续费及利息为非法经营数额。
二审法院认为:
上诉人韩某峰等人未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为赚取利润利用自营平台经营期货业务,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上诉人陈某澜负责购买软件、出资等事宜;上诉人郭某旭、戚某龙、胡某耀、原审被告人谭某明知韩某峰等人从事违法犯罪活动,仍在韩某峰等人的安排下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韩某峰等人设立山东期某公司,在未取得期货经营资质的情况下,招聘业务员开展期货业务,后财某期货公司济南营业部于2018年7月26日取得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可证。涉案数额应为涉案单位取得期货经营业务许可证之前投资人的投资数额,在此期间,韩某峰等人共计收取投资人“投资款”610余万元,涉案数额应以此认定……鉴于五上诉人于二审期间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可依法从宽处理,对淮北市人民检察院的量刑建议,本院予以采纳。违法所得应依法追缴。
【裁判结果】
一、维持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603刑初492号刑事判决的第五项、第七项……
二、撤销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2019)皖0603刑初492号刑事判决的第一、二、三、四、六项……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韩某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二十万元;
……
案件来源:韩某峰、陈某澜非法经营案【安徽省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皖06刑终164号】
09
非法经营个股期权证券业务,犯罪数额应根据被害人投资的数额计算
【裁判要点】
行为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伙同他人非法经营个股期权证券业务,犯罪数额应当根据被害人投资的数额计算,而非只计算被害人投资的净损失。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刘某伟(另案处理)成立益某公司。2018年9月,在刘某伟的授意下,由李某杰(另案处理)出面购买盈某汇公司和道某公司,以盈某汇和道某的名义面向社会不特定人群吸引客户开展个股期权业务。本案被告人徐某京担任市场部一部一组业务组长,业务员为被告人李某梦等人。
益某公司在没有相应的金融业务资质、缺乏资金第三方存管机制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平台、微信群等大量招揽客户,宣称为投资者提供场外个股期权交易服务,投资者在该公司自己开发制作的App软件中进行下单操作,选择操作标的并接受期权报价(即权利金)后,若行权日个股价格高于约定价格且上涨金额大于权利金,则投资者盈利,若上涨金额小于权利金或个股出现下跌,则投资者损失部分或全部权利金。各被告人为了取得客户信任,向客户发送由公司合规部制作的虚假盈利截图,通过夸大盈利、隐瞒风险等欺骗手段,诱使客户购买个股期权。
经审计,2018年8月至2019年5月期间,益某公司共吸收430名客户进行投资,总额为69808266元。其中,徐某京负责的团队经办客户期权费用合计17403393元,共计取得薪资报酬49237.45元、提成收入284793.13元。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梦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二万元……后李某梦等人不服,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伙同他人共同非法经营个股期权证券业务,犯罪数额应当根据被害人投资的数额计算还是只计算被害人投资的净损失?
辩护意见:
李某梦的辩护人提出,不应追究李某梦等业务员刑事责任;如追究刑事责任,犯罪数额应只计算客户投资的净损失。原判量刑畸重,建议二审纠正,考虑适用缓刑。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原判认定的非法经营犯罪数额。经查,非法经营犯罪侵害市场管理经济秩序,破坏社会安定,本案非法经营犯罪采用诱使被害人投资购买个股期权的方法,所获每笔投资的行为方式均系对市场经济秩序的侵害,评价该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应当包含被害人的每次投资,犯罪的数额应当根据被害人投资的数额计算。被害人实际盈利与否并不影响非法经营社会危害性的认定,且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只有极少数被害人投资能够盈利,绝大部分被害人都是一次性赔光。故原判以每一次投资的金额之和认定犯罪数额,并无不当。上诉人李某梦的辩护人提出“犯罪数额应只计算客户投资的净损失”,该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裁判结果】
一、维持灵宝市人民法院(2019)豫1282刑初442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十一项。即原审对被告人徐某京、王某、李某梦、孔某宝、于某的定罪量刑……
……
案件来源:徐某京、李某梦非法经营案【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豫12刑终97号】
10
设立公司以非法经营场外股权期货业务为主要活动,且公司财产与个人财产混淆,应认定为个人犯罪
【裁判要点】
行为人投资设立公司后,以非法经营场外股权期货业务为主要活动,且公司财产与相关个人财产混淆,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而应认定为个人犯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8年3月,刘某、周某、李某、唐某以亨某公司的名义开展非法的场外股权期货经营活动。刘某等四人未经国家主管机关批准,指使下属采用电话营销的方式,以低于正规期货交易所的开户及交易条件、帮助客户配资等为诱饵,大肆招揽投资人,通过由泽某公司实际运营的“金某期权”等App平台,进行场外股票期权交易。同时,提供代办开户、行情分析、推荐交易等服务。为此,刘某等人可从泽某公司处获取投资人入账“期权费”的45%至47%作为介绍返利款。
经核查,2018年6月至2019年3月间,刘某等人以亨某公司名义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数额达人民币2,000万元左右。刘某个人获利90万余元,周某个人获利90万余元,李某个人获利130万余元,唐某个人获利130万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周某、李某、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判处周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判处李某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三十万元;判处唐某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宣判后,刘某、周某、李某等人不服,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投资设立公司以非法经营场外股权期货业务为主要活动,且公司财产与相关个人财产混淆,应认定为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
辩护意见:
上诉人李某辩称:本案应为单位犯罪,其系从犯,不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原判量刑过重。
二审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刘某、周某、李某、唐某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与他人共同非法经营期货业务,扰乱市场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且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均应予惩处。四名原审被告人如实供述罪行,并在家属协助下退缴了全部或部分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经查,亨某投资以非法经营场外股权期货业务为主要活动,且公司财产与相关个人财产混淆,故本案不应认定为单位犯罪……综上,上诉人李某、唐某的相关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本院均不予采纳……但一审判决对唐某判处罚金90万元,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
【裁判结果】
一、维持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刑初1812号刑事判决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
二、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6刑初1812号刑事判决的第四项,即被告人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九十万元。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四十万元。
案件来源:李某、唐某等非法经营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02刑终459号】
11
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在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行为人将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成微信、支付宝账号生成二维码,录入雇佣他人开发的资金支付结算系统,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8年4月起,被告人郑某明、邹某强通过网络大量购买公民个人信息,交由柴某公司注册支付宝账号并生成二维码,后将二维码提供给客户用于洗钱中的资金流转,柴某公司抽取流水总额0.03%作为抽成。之后,郑某明、邹某强又将柴某公司产生的二维码提供给上海的某支付公司用于资金流转,柴某公司从中抽取流水总额0.15%作为抽成。
同年7月,郑某明雇佣并要求被告人张某聚开发一个多个网上商城端口接入一个支付系统的系统,张某聚在明知柴某公司没有资金支付结算资质且打算为博彩公司提供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况下,为柴某公司开发了第三方资金支付结算系统——“古某系统”,并伙同他人为该系统提供维护服务。期间,郑某明、邹某强通过网络及发放传单的形式推广柴某公司的资金支付结算通道,并通过网络联系多家博彩公司来使用柴某公司的“古某系统”进行资金支付结算。
经审计,2018年5月至2019年4月期间,柴某公司为他人提供非法资金支付结算的流水总金额达892930291.74元,获利总金额达28434076.60元。
一审法院认为,郑某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五百万元;被告人邹某强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二百万元……宣判后,郑某明、邹某强等人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经查,在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的情况下,上诉人郑某明、邹某强等人先将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注册成微信、支付宝账号,并生成二维码录入雇佣原审被告人张某聚开发的”古某系统”,博彩公司平台上的玩家发起充值时,平台会随机调用”古某系统”内的收款二维码进行扫码付款至相应二维码绑定的账户,柴某公司经过统计并收取相应的手续费后,将相关资金通过”古某系统”支付给博彩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构成非法经营罪。同案人卢某的供述、原审被告人吴某雄的供述及银行交易流水等证实上诉人郑某明、邹某强等人通过购买的方式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整理、分类后加以使用,上诉人郑某明、邹某强等人的行为同时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依法应当实行数罪并罚……
【裁判结果】
一、维持(2020)闽0302刑初12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第八项、第十项、第十一项、第十二项、第十三项、第十四项、第十五项、第十六项、第十七项、第十八项、第十九项、第二十项、第二十一项、第二十二项……
……
案件来源:郑某明、邹某强等非法经营案【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闽03刑终604号】
12
以虚构交易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为单位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非法资金提供支付结算业务的,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从事虚构交易,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非法为单位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非法资金提供支付结算业务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6年6月至2019年6月间,被告人刘某某利用实际控制的上海迪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某公司)、上海上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某公司)等18家公司,从上游取得支付牌照的“盛某”、“开某通”等第三方支付公司和民某银行等相关银行、银联签约,取得线上收单权限、资金代清算权限及网络接口,将网络接口接入支付服务器,搭建资金的支付通道,实现资金的线上收单和代清算的完整功能。
刘某某等人通过发展下游商户并与其签订合作协议,向下游商户提供网络支付接口,下游商户通过网络支付接口向“迪某公司”支付服务器发送支付交易指令进行资金支付操作,实现资金快捷支付结算。大量资金通过利用虚假交易、向“迪某公司”支付服务器发送支付交易指令的方式实现快捷转移,其中包含有大量的诈骗等非法活动资金。
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认定,“迪某公司”、“上某公司”的前述行为系无证从事支付业务。
争议焦点:被告公司的行为是否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辩护意见:
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提出:
第一,《刑法》和《非法支付结算司法解释》规制的非法支付结算是非持牌机构实施的资金“二清”型的支付结算业务,并未将所有的行政监管层面的支付领域违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
第二,本案基本业务模式与传统合规第三方支付、资金“二清”非法支付结算业务模式具有的显著区别,主要从事交易信息传递处理,部分涉及资金“二清”。
第三,本案非法经营数额应根据业务模式区分资金流和信息流,以案涉公司使用自有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移的资金数额为认定依据。
法院认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认定与上述事实确认,被告单位从事了司法解释确定的“虚构交易”,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非法为单位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的非法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构成非法经营罪。其非法资金支付结算(非法经营)额不能以被告单位的内部账户流转额或支付指令的交易额为区隔,而是应当看其所代为支付或通过其搭建的支付通道所支付的资金,是否符合二高司法解释确定的非法资金支付结算的情形为准。本案违法所得数额的认定,并没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对违法所得应作广义上的理解,应包含经营成本在内的所有数额,因本案重新审计鉴定后,明确了具体的获利数额,其经营成本没有,也难以界定,因此,本案的违法所得以在审理期间重新鉴定的数额为准。综上,对被告人刘某某的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不予采信。
【裁判结果】
一、被告单位上海迪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二百五十万元;
二、被告单位上海上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犯非法经营罪,判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五十万元;
三、被告人刘某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万元;
……
案件来源:上海迪某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上某数据服务有限公司非法经营一审刑事判决书【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2020)鄂0984刑初240号】
13
未获得支付结算许可,搭建“第四方支付”平台,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非法“第四方支付”平台为获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国家支付结算许可的情况下,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9月,被告人林某甲以某科技公司名义,在未获得支付结算业务资质的情况下,伙同被告人林某乙、张某等人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接口,自建支付结算系统,利用向他人收买、公司员工注册、下游商户提供等方式收集的大量无实际经营业务的空壳公司资料在某支付平台注册了数百个公司账户,再将支付接口散接至上述账户。
经审计,林某非法从事赌博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结算资金共计人民币46.69亿余元。
一审法院认为,林某甲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千万元……后林某甲等人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被告人林某甲、林某乙、李某乙、金某、张某、王某、吴某、黄某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
【裁判结果】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来源:林某甲等非法经营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刑终406号】
14
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有人直接套现,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使用POS终端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有人直接支付现金,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自2009年3月22日至2009年5月31日,被告人吴某明租用某商户申领的2台POS终端机,以虚构交易等方式向信用卡持有人直接支付现金,套现金额达人民币438754元。
2009年9月到2010年6月9日间,吴某明与同案人孙某楷共同使用POS终端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有人直接支付现金人民币金额为6550096元。
在此期间,吴某明违法所得累计人民币50000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吴某明违反国家规定,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使用POS终端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向信用卡持有人直接支付现金人民币金额为6988850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应依法惩处。其归案后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较重罪行,系自首;审理中自愿认罪,并退出部分非法所得。综上,依法对被告人吴某明减轻处罚,并可给予一定的缓刑考验期限。仪征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吴某明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指控罪名成立,应予支持。
【裁判结果】
一、被告人吴某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二、被告人吴某明退出的非法所得人民币五万元、作案工具POS终端机2台,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案件来源:吴某明非法经营案【江苏省仪征市人民法院(2012)仪刑初字第0072号】
15
以虚构交易的方式为他人提供“信用卡养卡”服务的行为,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通过虚构交易,以通过向持卡人的信用卡先还款再刷卡将所还款项套出的方式进行“养卡”,非法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4年至2015年期间,被告人袁某超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其本人或他人的商户终端机具(POS机),以虚构交易的方式,通过向持卡人的信用卡先还款再刷卡将所还款项套出的方式进行“养卡”,先后替陈某、朱某、王某等多人共计八十余张信用卡进行“养卡”,“养卡”金额累计达人民币1100余万元。
争议焦点:以虚构交易的方式他人提供“信用卡养卡”服务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辩护意见: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某超犯非法经营罪缺乏法律依据,根据《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POS机)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现金退货等方式向信用卡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情节严重的,应当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该解释处罚的具体行为是信用卡套现,“信用卡套现”中刷信用卡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得银行的现金而“信用卡养卡”的目的是让持卡人不产生利息和逾期利息,据此,本案持卡人和养卡人不是同一人,被告人袁某超仅仅帮持卡人养卡,并没有向持卡人直接支付现金,也就是他没有实施信用卡套现的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规定就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
法院认为:
本院认为,被告人袁某超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以虚构交易的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累计金额达人民币1100余万元,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被告人袁某超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予以从轻处罚。被告人袁某超积极退缴违法所得,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某超犯非法经营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辩护人关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某超犯非法经营罪缺乏法律依据的辩护意见,经查,被告人袁某超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销售点终端机具,以虚构交易的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情节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故此辩护意见,本院不予以采纳。
【裁判结果】
一、被告人袁某超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
案件来源:袁某超非法经营案【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2017)苏0583刑初752号】
16
在法定的交易场所以外购买外汇,即使外汇是他人骗购得来且行为人并不知情,仍属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裁判要点】
买卖外汇只能在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进行,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购买外汇,即使外汇是由他人骗购得来,且行为人并不知情,仍属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7年2、3月,被告人熊某在澳门赌场认识了被告人姚某华,双方商量由熊某提供港币给姚某华。熊某与被告人张某商议帮姚某华兑换港币的事宜,熊某、张某主要通过朋友或在微信上对外发布需要兑换港币的信息招揽客人,买卖他人每年每人享有的年度便利化额度(5万美金)以“境外旅游费”在银行进行分拆购付汇,事成后向客人及介绍人共支付报酬300元人民币。
姚某华每次需要兑换港币时,通过其在珠海市开设的银行账号将人民币转至熊某、张某指定的银行账号后,张某便与招揽到的客人约至珠海市,随后通过笔记本电脑登录客人的网上银行购买港币,再将港币转账至姚某华指定的澳门银行账号。姚某华在澳门接收到港币后用于换购给游客牟利。
截至案发,张某、熊某共招揽到约200名客人,向银行共骗购了70532447元港币,并将该70532447元港币全部转账至姚某华指定的澳门银行账号。张某、熊某非法获利约6万元人民币。
一审法院认为,姚某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十万元。随后,姚某华提起上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购买外汇,但不知晓外汇是他人骗购得来,是否属于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辩护意见:
姚某华的辩护人提出:上诉人姚某华从张某、熊某等人处购得的港币全部是外汇交易指定银行中国银行转账交付,姚某华并不“明知”张某、熊某的港币是骗购而来,原判决定性有误,上诉人姚某华没有“非法经营”的行为,不应认定其犯非法经营罪。
二审法院认为:
经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非法买卖外汇,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买卖外汇只能是在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没有资质不能经营外汇买卖。本案中上诉人姚某华购得港币的对象是上诉人张某、熊某,并在澳门向游客出售港币,张某、熊某仅是通过中国银行转账渠道将港币汇至上诉人姚某华指定的澳门账户内,并非上诉人姚某华直接与中国银行交易购汇供自己使用,即上诉人姚某华购买外汇是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以外,不论其是否知道上诉人张某、熊某的外汇是骗购得来,均属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本院认为,上诉人姚某华、张某、熊某违反国家规定,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非法经营数额达港币70532447元,属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结果】
一、维持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刑初1704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四项、第六项。
二、撤销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2018)粤0402刑初1704号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第五项、第七项。
三、上诉人张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四、上诉人熊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
案件来源:姚某华、张某非法经营案【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4刑终60号】
17
行为人通过境外收付美元,境内再收付相应数额的人民币的方式实现价值转换,属于变相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裁判要点】
行为人安排境外收付美元,境内再收付相应数额的人民币,实则是以外汇和人民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属于变相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6年11月至2018年11月,被告人邹某容应他人要求,未经批准在深圳市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帮客户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或者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从中赚取汇率差。被告人邓某峰明知邹某容未经批准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帮助他人经邹某容将美元兑换成人民币或者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从中赚取汇率差。邹某容使用其名下或者控制的银行账户,收取兑钱资金72150795.03元。邓某峰使用其名下的银行账户支付兑钱资金37725010.50元给萧某,支付兑钱资金13882509元给曹某文,支付兑钱资金4972238元给李某。
2017年至2018年10月,被告人康某台未经批准在广州市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帮客户将人民币兑换成美元。康某台收取客户人民币后,让他人将美元汇入客户指定账号,从中赚取汇率差。康某台使用其名下的银行账户收取兑钱资金26299910元。
一审法院认为,邓某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康某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钦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安排境外收付美元,境内再收付相应数额的人民币,属于非法买卖外汇还是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
抗诉意见:
钦南区人民检察院抗诉认为:本案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0号)只是对骗购外汇和非法买卖外汇作出司法解释,并没有对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作出司法解释,原判依据此司法解释在五年有期徒刑幅度以下对康某台、邓某峰进行判决并适用缓刑,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二审法院认为:
关于资金支付结算业务和买卖外汇认定问题。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的规定,非法买卖外汇主要包括倒买倒卖外汇、变相买卖外汇等情形。倒买倒卖外汇,主要指行为人在国内外汇黑市进行低买高卖,从中赚取汇率差价的行为;变相买卖外汇,主要指行为人在形式上进行的不是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直接买卖,而是采取以外汇偿还人民币或以人民币偿还外汇、以外汇和人民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的资金跨国(境)兑付行为。资金跨国(境)兑付是一种典型的变相买卖外汇行为。资金跨国(境)兑付型地下钱庄,不法分子与境外人员、企业、机构相勾结,或利用开立在境外的银行账户,协助他人进行跨境汇款、转移资金活动。
本案中,康某台、邓某峰、邹某容安排境外收付美元,境内再收付相应数额的人民币,实则是以外汇和人民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属变相的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故抗诉机关认为本案属于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20号)与本案无关的抗诉意见不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邓某峰、康某台、邹某容违反国家规定,实施非法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非法经营数额均达人民币二千五百万元以上,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结果】
一、维持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702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第三项对原审被告人邹某容的定罪和量刑……
二、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法院(2020)桂0702刑初147号刑事判决书第一项、第二项……
三、原审被告人邓某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
四、原审被告人康某台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案件来源:邹某容、康某台、邓某峰非法经营案【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桂07刑终163号】
18
明知他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业务,仍为其积极提供帮助,涉嫌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行为人明知他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活动,为他人顺利完成非法买卖外汇交易,大量提供他人银行卡,并使用其掌控的银行卡,为他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交易积极提供帮助,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2年2月、3月,被告人刘某通过他人认识了黄某。在明知黄某系从事地下钱庄生意(买卖外汇)的情况下,仍然帮助黄某组织大量中国公民开办银行卡帮助其完成地下钱庄的转账交易,以规避中国银行组织对外币汇兑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监管。刘某还按照黄某的指示,利用自己的或者组织他人开办的银行卡接收黄某转账过来的买卖外汇款,再通过上述中间账户将买卖外汇款转账至买卖外汇人的中国大陆账户,帮助完成地下钱庄交易,且在自己提供的大陆账户出现故障时,出面处理,维护账户的正常运行。
刘某在常德地区组织开办的97个银行卡账户,共计转入资金人民币135559.60369万元(约20186.678732万美元),共计转出资金人民币135243.348782万元(约20139.584052万美元);刘某在湘潭地区组织开办的34个银行卡账户,其中6个银行卡账户共计转入人民币9343.663132万元(约1346.931401万美元),转出人民币9345.331331万元(约1347.171880万美元);刘某在中山地区组织开办的近三百张银行卡,其中80个银行卡账户共计转入人民币104635.22731万元(约16056.885971万美元),转出104578.855561万元(约16048.235398万美元)。
一审法院认为,刘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五万元。宣判后,刘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经查,证人马某一、黄某平的证言及刘某的供述证实刘某在2012年认识黄某并用自己的银行账户为黄某转账时已知其从事非法买卖外汇生意,仍为其提供帮助,刘某具有非法经营的主观故意;刘某的银行账户交易记录、手机短信记录、台式电脑勘验报告、证人侯某云、王某林、马某花等人证言、金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员工练某梅、张某龄等人的证言证实金某房地产中介有限公司负责人系刘某,收寄银行卡及测试、建立台账、转账均系刘某独自操作,给他人的办卡费用亦由刘某支付,并提取人民币现金安排马某一交给黄某的人,为黄某顺利完成非法买卖外汇交易逃避监管大量提供他人银行卡,并使用其掌控的郝某华、马某香等人的银行卡为黄某从事非法买卖外汇交易积极提供帮助,刘某实施了非法经营的客观行为,其行为已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应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裁判结果】
一、维持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7)湘0702刑初54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二、撤销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17)湘0702刑初54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刘某犯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定罪、量刑部分。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五万元。
案件来源:刘某非法经营案【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湘07刑终326号】
19
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违法所得数额难以确定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的千分之一认定违法犯罪数额,并处或单处相应罚金
【裁判要点】
行为人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违法所得数额难以确定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的千分之一认定违法犯罪数额,依法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20年5月26日,某电气公司被诈骗73万元,该笔资金经多番流转至高某洲银行账户。2020年5月份,高某洲(另案处理)通过他人兑换美元,将人民币汇入他人指定的被告人刘某工商银行账户3854400元、揭某(另案处理)建设银行账户7647850元,再通过刘某、揭某银行账户转入被告人马某明持有的农业银行账户。马某明在自己名下银行账户因兑换美元被公安机关冻结的情况下,又利用自己堂弟、母亲的银行账户继续从事非法兑换美元业务。
其中,马某明在国家规定的交易场所之外,将其持有的账户内资金共计25710045元人民币兑换美元后汇入境外指定帐户,马某明个人违法所得2.4万元。刘某用其账户、揭某账户转账共计17112582元人民币给马某明持有的银行账户用于兑换美元。
一审法院认为,马某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刘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宣判后,马某明、刘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某明、刘某违反国家规定,实施变相买卖外汇行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其行为均已构成非法经营罪。其中马某明系情节特别严重,刘某系情节严重……关于马某明、刘某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判罚金过高的上诉理由和辩护意见,经查,本案马某明违法所得系2.4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刘某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义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的规定,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义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违法所得数额难以确定的,按非法经营数额的千分之一认定违法犯罪数额,依法并处或单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原判判处罚金无法律依据,故该上诉理由与辩护理由本院予以采纳。综上,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审判程序合法,但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罚金不当,本院依法予以纠正。
【裁判结果】
一、维持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2刑初904号刑事判决第三项。
二、撤销河南省南阳市宛城区人民法院(2020)豫1302刑初904号刑事判决第一、二项。
三、上诉人(原审被告人)马某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二万元。
四、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八万元。
案件来源:马某明、刘某非法经营案【河南省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豫13刑终145号】
20
提供真实的交易平台和账户,并通过借款协议出借资金,由客户自主完成期货交易,仅收取配资利息及手续费的,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要点】
行为人提供真实的交易平台和账户,并通过借款协议出借资金给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由客户自主完成期货交易,按照借款协议收取利息、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等进行牟利的,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裁判思路】
基本案情:
2014年11月21日,被告人周某设立沃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12月至2015年5月期间,沃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及法人周某在未取得期货经营许可,也未取得其他期货公司授权经营的情况下,利主账户以及交易软件,开立出杨某、伍某的期货交易个人账户,从“某期货有限公司”开立出的陈某、张某、贾某波的期货交易个人账户提供给客户在“众某金融资产管理平台”进行股指期货交易(买涨买跌),同时周某为客户使用的个人账户提供配资(即配备期货交易所需资金),为客户的个人账户进行风险控制(即设置强制平某线),提供技术支持等,并收取配资月利息1.2%至1.5%,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等进行牟利。
一审法院认为,周某利用“众某金融资产管理平台”开立“分账户”供客户使用,从而实现掌控自己出借资金的风险,当客户资金亏到“设定值”时,周某按照“借款协议”进行“平仓”(停止客户进行期货交易),其行为实质上是“配资”行为,即出借资金给客户进行期货交易行为,且期货交易都是客户自主完成,是在未脱离“主账户”的合法交易,周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后检察院提起抗诉。
争议焦点:行为人提供真实的交易平台和账户,并通过借款协议出借资金给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由客户自主完成期货交易,按照借款协议收取利息、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等进行牟利,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
抗诉意见:
检察院抗诉认为:被告人周某虚构从事配资业务资质,向社会不特定的人提供由自己掌控的非法“期货配资”业务。被告人周某从事“期货配资”为了赚取客户的利率,直接使用主账户扣除客户从事期货交易的“每手交易”手续费牟利,而且在提供“配资业务”中收取被害人较高额的利息。致使客户会被迫进行交易,提高了交易操作风险,被告人周某则可以“稳赚不赔”。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从而导致对被告人周某量刑不当。故依法提起抗诉,请二审依法判处。
二审法院认为:
经查,《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期货”是指有关公司或个人未经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擅自设立或者变相设立期货交易场所、期货公司及其他期货经营机构,或者擅自从事期货业务,或者组织变相期货交易的活动。
本案中,原审被告人周某利用其他公司合法开立的期货交易主账户,通过“众某金融资产管理平台”交易软件开立“分账户”供客户使用,并出借资金给客户进行期货交易,期间的期货交易行为均由客户自主完成。周某为了实现掌控自己出借资金的风险,当客户资金亏到“设定值”时,周某按照“借款协议”进行“平仓”(指停止客户进行期货交易)。综上,周某提供真实的交易平台和账户,由客户自主操作完成期货交易行为,按照借款协议收取利息、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等进行牟利。其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非法经营期货”,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原审判决根据公诉机关庭审举证的证据对此事实进行认定,并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原审被告人周某宣告无罪并无不当。故对此抗诉意见本院不予支持。
本院认为,原审被告人周某将其他公司设立的期货交易账户提供给李某、宋某等人进行股指期货交易,并通过借款协议向李某、宋某等人提供配备期货交易所需资金,收取配资利息及股指期货交易手续费等进行牟利。其行为不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非法经营期货”,原审法院根据“罪行法定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对原审被告人周某宣告无罪正确,检察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
【裁判结果】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案件来源:周某非法经营二审案【湖北省咸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鄂12刑终289号】
三、实务建议
非法经营罪作为行政犯,在很多经营者看来,“其从事的业务顶多也就是行政违法,大不了监管部门罚款即可,凡是钱能解决的事都不是事”。正是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对企业经营者而言,作为“口袋罪”的非法经营罪的刑事风险可谓防不胜防。为防止行为人触犯非法经营罪,我们在对重点案例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办案经验,提出以下建议。
(一)充分认识场外配资行为的违法性
在很多人看来,场外配资无非就是“借钱炒股”,是一种民间借贷行为,与违法犯罪不沾边。然而,场外配资行为不等同常见的借贷行为,已经受到非法经营罪的规制。
场外配资是指未取得经营证券业务资质的配资平台,以营利为目的,利用计算机软件系统的二级分仓功能等方式将资金超出借给资方进行证券交易,通过收取保证金、享有平仓权等方式保证配资不受损,并赚取利息、费用或收益分成的行为。如本文在实务解析部分提及,场外配资包含系统分仓模式、出借账户模式、客户账户模式,该三种模式都涉及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即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进行证券交易,并通过收取担保物等方式保证融资不受损失。
于2019年修订、2020年3月1日生效实施的《证券法》第一百二十条明确规定,证券融资融券业务属于证券公司特许经营业务。自此,场外配资行为被列入非法经营罪规制范围之列。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指出:“加强场外配资监测,依法坚决打击规模化、体系化场外配资活动。”结合《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二)》,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数额在100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即构成非法经营罪。
(二)充分了解期货交易的认定标准
在非法经营期货业务的相关案例中,部分展业公司利用现货之名,从事期货之实。从司法实践来看,在涉嫌非法经营期货类案件的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或被告单位从事的究竟是现货交易还是期货交易往往成为争议焦点,因此了解期货交易的认定标准、有效界分现货交易与期货交易尤为关键。考察是否属于期货交易应当结合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的判断标准,如果同时具备,那么将被认定为属于期货交易。
关于形式要件,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如果具有集中竞价、标准化合约、保证金交易、每日无负债结算、对冲交割等内容,即具备期货交易的形式要件。
关于实质要件,可以从交易目的、交易功能、交易主体进行综合判断。首先,不同于现货交易以转让标的物所有权为核心,期货交易的目的在于转移价格风险,获取投资利润,一般无需实物交割。其次,现货交易主要承担商品流通功能,通常发生于特定的买卖主体之间,流通性较差,而期货交易具有价格发现、投资套利主要功能,流通性较强。最后,在现货交易中,交易平台仅提供基础信息,不提供担保,而在期货交易中,交易所为期货交易提供履约担保。
(三)未经许可不得从事支付结算业务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支付结算业务(也称支付业务)是商业银行或者支付机构在收付款人之间提供的货币资金转移服务。在我国,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是金融特许专营业务,无论是以金融机构为主的传统支付结算业务,还是以非金融机构为主的新型网络支付结算业务,都必须经过金融主管部门的批准。其中,非银行机构从事支付结算业务,应当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未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而从事支付结算业务的行为,情节严重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不断发展,网络支付结算已成为主流。由于我国对第三方支付平台监管严格,部分第四方支付机构非法对外提供支付结算业务。“第四方支付”又称“聚合支付”,是指通过聚合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银行、合作电信运营商及其他服务商接口等多种支付工具进行的综合支付服务。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发布的《关于开展违规“聚合支付”服务清理整治工作的通知》,聚合技术服务商严格定位于收单外包机构,不得从事资金结算等业务,不得以任何形式经手特约商户结算资金,从事或变相从事特约商户资金结算。司法实践中,如果第四方支付平台在未获得支付业务许可的情况下,不仅提供接入支付接口服务,还要在平台所控制的账户内形成“资金池”,经过平台转移客户所充资金,将涉嫌非法经营罪。
(四)转变“信用卡非法套现未谋取非法利润就不构成犯罪”的错误观念
实践中,部分行为人认为其虽然实施了非法套现的行为,但没有谋取非法利润,没有扰乱市场秩序,就不构成犯罪,实则是对非法经营罪的误读。我国《刑法》之所以将信用卡非法套现行为列入非法经营罪的客观行为之中,是因为信用卡非法套现行为侵害了持卡人、银行的资金安全,破坏了信用卡的发行与管理秩序,将银行原本鼓励的消费行为变为取现、借贷行为,绕开了银行针对取现、借贷行为设定的高额费用、透支利息和额度限制,使得银行的资金无息无手续费的流出,对银行资金安全、金融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因此,行为人是否谋取了非法利润不影响非法经营罪的成立,其实施的非法套现行为在事实上已经谋取了银行给予的潜在经济利益,即变相将信用卡的授信额度转化为现金,从而将金融机构资金置于高风险之中,扰乱了国家金融管理秩序,构成非法经营罪。
(五)远离非法外汇买卖
我国对外汇经营业务实行专营制度,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只有在经过国家的特别许可以后才能从事此种业务,未经许可不能经营外汇买卖,在外汇指定银行和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及其分中心以外买卖外汇,即破坏了国家的外汇专营制度,涉嫌非法经营罪。
值得重视的是,有些人认为非法经营罪仅惩治卖外汇的行为,购买外汇可“高枕无忧”,然而司法实践判例表明,非法经营罪对“卖外汇”和“买外汇”的行为进行双向打击,如果行为人以卖为目的购买外汇,即使尚未卖出,买外汇的行为实际上是倒买倒卖外汇行为的组成部分,应当认定为非法买卖外汇行为。
另外,除了“卖方”和“买方”涉嫌本罪以外,为“卖方”或“买方”提供帮助的行为人有可能被认定为共犯。例如,如果明知他人从事非法买卖外汇活动,仍为他人提供大量银行卡,并使用银行卡帮助他人接收、转账外汇款,构成非法经营罪。
(六)打破“投资设立的公司涉嫌非法经营属于单位犯罪”的错误认识
自然人与单位都可以构成非法经营罪,因此实践中关于犯罪行为究竟定性为个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是较为常见的争议点。通常而言,区分单位犯罪还是个人犯罪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判断,即是否体现单位的意志,由单位决策机构集体决定;是否以单位的名义实施;利益是否最终归属于单位。如果同时符合,通常情况下可能被认定为单位犯罪。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明确规定以下三种情形不以单位犯罪论处,而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论处:(1)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2)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3)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因此,对于想要通过投资设立公司来实施非法经营犯罪行为的股东而言,公司并不能成为其逃避法律责任的避风港。
韩帅 《金融刑事风控实战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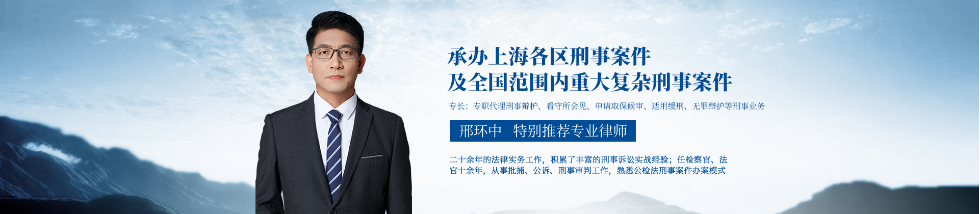


会员登录关闭
注册会员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