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实践中,经常会遇到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到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能否认定自首的情况,刑法理论界及实务部门的意见存在分歧,目前也尚未有统一的法律指导性文件,实际操作中也在一直存在争议。
我们先分析一下什么是传唤,传唤是司法机关通知诉讼当事人于指定时间、地点到案所采取的一种措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对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犯罪嫌疑人所在市、县内的指定地点或者到他的住处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对在现场发现的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但应当在讯问笔录中注明。”从法律规定上可以看出当场传唤犯罪嫌疑的两种方式:一种是书面形式,即用传唤证或传票来传唤犯罪嫌疑人;一种是非书面形式,即口头传唤。但在实践中,侦查机关也经常电话传唤或捎带口信传唤犯罪嫌疑人。
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等司法解释和法律文件中,对自首的各种情形分析得很详细,这里不再详引。但可以看出,自首最显著的两个特点是: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
那么,犯罪分子经传唤到案是不是自动投案?如果到案后还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那么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认定自首?这是司法实践中控辩经常双方争论的焦点。下面结合笔者几年来办理的相关案件,对被传唤人经传唤到案的几种情形能否认定为自首作以简要论述。
首先是侦查人员找到犯罪嫌疑人,当场送达传唤证后带其到案或在犯罪现场发现犯罪嫌疑人,口头传唤并带其到案,如果该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时,如实供述,能否认定自首。张某系某国有企业中层干部,负责管理该企业建设工程款,在履行职务过程中,贪污工程款80万元,用于其个人股票经营,后被举报。侦查人员通过核查工程帐目及股票帐户后发现,张某确从其负责管理的帐户内转移出80万元放到自己及其家属的股票帐户内用于买卖股票获利。在掌握其犯罪事实及相关证据后,侦查人员在张某的办公室向其送达了传唤证,并将张某带回侦查机关讯问,张某如实供述。另一个案例是李某在火车站内因插队购票与另一旅客发生争执,并将对方打成轻伤,被害人报警,在李某买完票后即将离开车站时,经被害人及证人指认,警察以口头传唤的方式将李某带回车站派出所讯问,李某如实供述。以上两个案例虽然传唤的方式稍有不同,张某是经传唤证传唤,李某是经口头传唤,但均是犯罪嫌疑人经传唤后被侦查人员带回侦查机关,到案后也均如实供述。能否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张某和李某均系在归案前,侦查机关就已经掌握了其主要犯罪事实,也有相关的证据予以证实,侦查人员当场送达传唤证或当场口头传唤并将张某、李某带到办案机关讯问,二人的到案缺乏主动性,所以即使到案后如实供述也不应当认定为自首,但可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认定为坦白。再一个案例是公安机关接群众电话举报称王某盗窃铁路运输原煤,侦查人员到王某家中找到王某,并在仓房内发现原煤,疑似赃物,遂将王某口头传唤到公安机关讯问,王某主动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这个案例中的王某是否可认定为自首?笔者认为,王某归案前,公安机关所掌握的仅仅是王某可能犯罪的一些犯罪线索,并没有确凿的证据定案,基于该线索找到王某,王某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自己的罪行,公安机关根据其供述印证的赃物,找到了运赃工具等证据,也就是说王某的供述对案件的侦破起到了重要作用,王某的到案及如实供述也证明其归案的主动性和如实供述的自觉性,因此,应当认定为自首。
其次是侦查人员掌握了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实与证据,打电话传唤或托他人捎带口信传唤,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罪行的是否可以认定自首,争议最大。吴某伙同赵某在火车站内停留的货车上盗窃大豆,被害单位报案后,经公安机关侦查取证,将此二人列为犯罪嫌疑人,去二人的居住地寻找未果,但通过邻居得知了吴某的电话,在赵某打工的工地找到了赵某的弟弟。于是侦查人员电话传唤吴某、托赵某的弟弟捎带口信传唤赵某,让二人到火车站公安派出所接受讯问。后来二人到派出所接受讯问,均如实供述。这个案件在处理时,合议庭的意见不统一。第一种意见是:被传唤人被司法机关电话传唤或捎带口信传唤到案,因公安机关已掌握了二人的犯罪事实及证据,所以二人的到案也属于被动归案,不能认定自首,因为传唤是司法机关讯问被传唤人的一种方法,具有不可抗拒的效力,若行为人拒绝传唤可以通过拘传强制其到案,故其到案缺乏主动性,不能认定为自首。第二种意见是,传唤是被传唤人接到传唤通知到案,不论是电话传唤还是捎带口信传唤,因传唤不是强制措施,所以二人的到案系自动、主动到案,且根据《解释》中的相关规定,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的,就是自动投案,其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应认定为自首。第三种意见是:能否认定二人自首,应视情况而定。如果二人到案后在未被讯问或讯问过程中,主动交代犯罪事实且愿意接受审理和追诉的,可以认定自首;如果二人接到传唤后心怀公安机关并并掌握其犯罪证据等侥幸,开始并不认罪,只是在讯问过程中迫于压力才交代的,表示其不是主动决定自首,不能认定自首。
笔者认同第二种意见,吴某、赵某是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或捎带口信传唤到案的,这种情况虽然与主动、直接向司法机关投案有所区别,但就应为自动投案,且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自首。理由是:首先,传唤是一种通知,不属于强制措施。被电话传唤或捎带口信传唤到案符合《解释》规定的“在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的时间段,属“自动投案”。其次,经电话或捎带口信传唤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具有成立自首所需的自动性和主动性。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话或他人捎口信得知自己被传唤后,应该知道自己的犯罪行为已经暴露或已开始暴露,已被公安机关怀疑,这时其自主选择的余地很大,可以选择接到传唤后到案心怀侥幸去脱罪或如实供述争取宽大处理,也可以选择拒不到案逃往处地来躲避刑事处罚,这两种情况无疑给司法机关破案带来了难度。而该案例中的吴某、赵某接传唤后,在侦查人员没在自己身边的情况下,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就表明了其认罪悔罪、愿意为自己的罪行承责的主观目的,具有了到案的自动性、主动性及如实供述性等成立自首的条件。《解释》中有“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视为自动投案”的规定,意思是说犯罪行为人犯罪后得知自己的罪行已被公安机关发觉,且被通缉、追捕时,主动到案,如实供述,成立自首。而本案中二位犯罪嫌疑人仅仅是受到电话或捎带口信的传唤,就自动、主动归案,如果这种情况不认定自首,也不合逻辑,更不符合立法的本意。换一种思维,如果此种情况不认定自首,那么我们假想一下,吴某和赵某接到电话或捎带口信传唤,得知自己的罪行暴露后潜逃,被通缉后又主动归案,如实供述,这种情况合议庭其他成员均表示系自首。那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潜逃去躲避刑事处罚,基于各种压力再自动投案的就认定为自首;接到电话或捎带口信传唤后,积极主动到案的并如实供述的,还不认定为自首,这就不合常理了,更不利于引导犯罪分子弃恶从善、从内心深处认罪悔改,而增长了犯罪分子钻法律空子的“积极性”。
总结以上论述,一种情形是侦查人员当场传唤被传唤人,无论是以送达传唤证还是以口头传唤方式,只要侦查机关掌握了其犯罪事实及证据,那么被传唤人的归案不能认定为自动投案,其如实供述也只能认定为坦白;但侦查机关掌握的证据材料仅仅是犯罪线索,需要被传唤人归案后的供述才能补强证据,顺利侦破案件,那被传唤人的到案并如实供述就应该认定自首。另一种情形是侦查机关电话传唤或捎带口信传唤被传唤人,被传唤人主动到案并如实供述,那么无论侦查机关是否全部掌握其犯罪事实及证据,均应认定为自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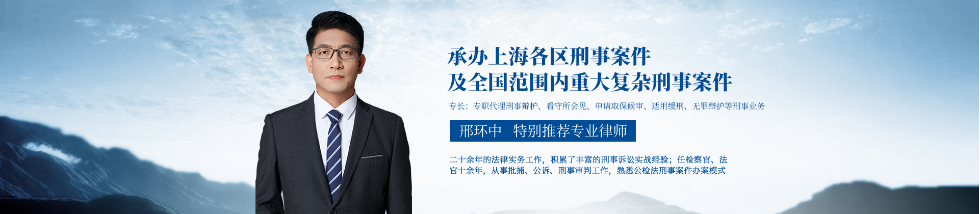


会员登录关闭
注册会员关闭